
我国一些邪教组织常常冒用基督教的名义,有三大最主要的原因。一是基督教自身的个体原则,使得邪教组织有足够的理论建构空间,可以任凭自身的需要,对经典文本进行理论建构,从而达到其目的。二是基督教作为西方传统宗教,与我国社会大众、尤其是农村大众有一定的距离,这也赋予其足够的活动空间,使其有一定的迷惑性,能够以基督教的名义,迷惑我国对基督教教义和理论了解不多的大量本土基督教信徒。三是冒用基督教的名义,能够迷惑西方的基督教徒和民众,这些人不理解中西方文化和历史的差异,误认为这些冒名的邪教只是宗教信仰的差异,而没有意识到其背后反社会、反人类的巨大危害。
1995年以来,我国先后认定的邪教组织共有23个。在这23个邪教组织中,冒用佛教名义的有5个,而冒用基督教名义的则达到令人惊讶的18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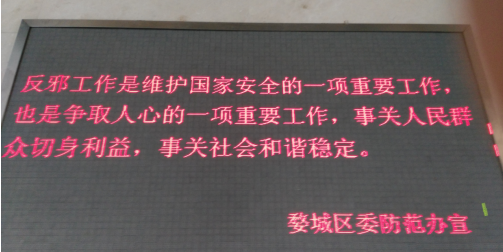
我国冒用基督教名义的邪教组织,除了通常的敛钱、骗色等劣迹之外,还具有两大基本特征。首先,它通常产生于自身的东方文化系统,主要源于中国大陆、港台和韩国等东方文化圈,即便是来自美国的“呼喊派”,其实质也是东方人自己的创造。其次,这些邪教通常不像西方的邪教那样常常争论核心教义,而是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以教义或经典为其政治目标服务,披着基督教外衣而又具有强烈的东方民间宗教的秘密结社色彩。
西方社会的宗教演变与邪教对其社会的影响
产生于公元之初的基督宗教,历经两千年,经历了两次大的分裂,形成了3个主要派别以及无数小宗派团体。这三大派别在我国分别被称为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教。在这三大派别之外,基督教从16世纪以来,内部又形成了六大宗,包括路德宗、圣公会、改革宗、浸礼宗、循道宗、公理会。而实际上,在这些传统的宗派之外,基督教数百年来不断更新繁衍,至今保守地估计,基督教有3000多个派别,还有人估计这个数字应该在两万左右。由美国哥顿康威尔神学院托德·约翰森等人所发布的2017年全球基督教状况报告显示,在全球75亿人口中,基督徒人口占33%左右,达24.7亿。在这24亿信徒中,天主教徒占了一半,达12亿多,而基督教徒、独立教会的信徒,以及其他无法归类的信徒占了11亿多。据相关统计,这些信徒分属的宗派和组织已经达到4.7万个。
16世纪新教改革最大的成就是打破了原来教宗的权威以及建立在这一权威基础上的教义、礼仪和思想的统一。一种新的权威原则,所谓的“人人皆祭司”的个体性原则代替了天主教的旧原则,个体取代了教会和教宗,成为新的信仰权威。对这一点,马克思有极为经典的论述:“它(新教改革)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却恢复了信仰的权威。它把僧侣变成了俗人,但又把俗人变成了僧侣。”马克思所谓俗人变成了僧侣,也就是以原来在宗教信仰中毫无权力的个体信徒取代了僧侣,掌握了宗教力量,尤其是解释经典的权力。这一权力使得信徒能够绕过教会和教宗的规定,按照自己的理解阐释《圣经》经文。理解的主观性造成了对经典解释的巨大差异,千人千面、万人万言,由此,一个统一的大教会分裂为无数的大小宗派。这种几乎毫无约束的解经自由度,使得教会的统一性自此分崩离析。当然,这也就意味着不可掌控因素的滋长,包括许多非法团体和邪教因此应运而生。
这一新的宗教模式在西方社会掀起轩然大波,改变了西方社会的整体面貌,整个西方为了这些宗教原因陷入了冲突和战争之中。法国基督教和天主教之间的胡格诺战争持续了30多年,造成了数次大屠杀。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新旧教两派间的30年战争是欧洲大陆第一次全面战争,使日耳曼邦国的一半男性埋葬在战火中。断断续续持续了上百年的宗教战争和宗教冲突直接动摇了欧洲的宗教一元化社会秩序,改变了欧洲社会的基本面貌。最后,在新大陆的弗吉尼亚土地上发展出宗教宽容原则,才解决了把欧洲拉入深渊的宗教冲突。宗教冲突的解决意味着欧洲放弃了其基本文化形态,建立了新的以现代启蒙哲学思想为基础的新欧洲。这个新欧洲以现代权利观念代替了原来的基督宗教信仰,形成了新的人权信仰。这一个体权利信仰实际上是新教改革个体信仰权威原则的延续,是在战争之后剥去宗教外衣的个体原则。这个原则的建立,意味着西方社会建立了人权新宗教,代替了原先的基督宗教信仰,意味着基督宗教不再是构建西方社会统一性的基础,也意味着基督宗教丧失了原先掌控的各种权力,不再是神圣的,更不再是不可侵犯的。
基督宗教丧失了其作为西方社会统一性的基础,就意味着它的分裂与否对西方社会已经不再重要,它的正确与否对西方社会也不再重要。无论什么样的异端或者邪教,无论怎样歪曲解释教义,都不会影响西方社会的统一性。宗教战争的历史也使西方国家放弃了对宗教的价值判断,不再尝试对宗教进行区分,而是试图保持中立。所以,西方社会往往无视其境内的邪教组织,而是将其视为纯粹的宗教或者心理问题,除非其造成了严重危害或触犯到具体的法律。据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心理学教授玛格丽特·辛格的报告,美国的邪教组织在2000个到5000个之间,卷入其中的有1000万人至2000万人。这些邪教有一个基本特点,它们继承了西方传统的宗教元素,尤其西方传统的宗教信仰问题,喜欢争论宗教教义问题,现代学者也往往从宗教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这些邪教团体。西方著名的“耶和华见证人”,其核心教义实际上是“亚流主义”的现代翻版,借此否定基督的神性,否定三位一体的传统教义。另一个“基督教科学派”也否定基督的神性,否定创造、堕落、救赎等传统教义,以精神性原则作为上帝的本质。这些邪教与传统主流宗教争论着神学和教义问题,通常对政治问题没有兴趣。而原来作为社会最高权威的宗教,早已在持续上百年的宗教战争中让出了自己的位置,这些邪教对传统宗教教义的挑战既不会影响西方社会的稳定,也很难威胁到西方的国家政治安全。
东方世俗社会面临的邪教挑战
与西方社会曾经的宗教一元论不同,中国社会自周朝以来就是人文化的世俗社会,其最高权威一直是世俗政权而不是宗教。因此,东西方同样是打着基督教名义的邪教组织,但在其基本取向上就体现出巨大差异。我国冒用基督教名义的邪教组织,一般也都是以对《圣经》的任意解释为基础。“呼喊派”所谓的《圣经恢复本》,就是按照自己的理解重新翻译和注释经典,将《圣经》中的“求告主名”理解为“呼喊”。
但是,与西方邪教组织喜欢争论深奥的教义问题不同,东方文化圈中冒用基督教名义的邪教组织往往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他们不喜欢纠缠于教义理论问题,而是借用宗教的外皮,以此作为达成其政治目的的手段。我国邪教的这一特征,与我国世俗化社会的基本形态是相符合的。如果说西方社会是以宗教为基础建立起社会统一性的话,东方社会的统一性基础则是世俗政权。这一政治文化共同体有一套基本制度以及制度背后的观念体系,用以塑造和指导共同体中的人群,其最高权力是政治权力,其神圣体现在最高政治领袖身上。东方文化的这一基本世俗特征,使得东方社会基本没有宗教战争,即便有宗教参与,也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政治战争。没有国家统一规定的宗教信仰,也没有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的宗教权力,这使得宗教信仰一开始就没有受到过多的社会关注。因此,冒用西方宗教名义的邪教组织,其实际兴趣也并不在宗教信仰本身,而是更注重现实利益,包括金钱、美色、权力乃至社会和政治权力。
因此,不限于西方社会的宗教学、心理学等对邪教理解的角度,我国社会还从政治学等现实角度理解邪教问题。在我国传播的冒基督教名义的邪教组织,几乎都有通过宗教名义获取非法世俗权力的企图。他们主要通过政治性的阐释基督教《启示录》,来表达这种政治企图。作为启示文学,《启示录》充满了象征性的语言和形象,充满了难以把握的阐释空间,传统基督教对于此卷经书相当谨慎,甚至避而不谈。与正统基督教的谨慎不同,邪教组织特别喜欢利用启示文学的这种象征性为自己的利益目标服务。邪教的政治冲动,严重威胁我国世俗社会的政治统一性基础,危害社会稳定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东方邪教组织强烈的政治冲动,是典型的世俗政治社会的产物。在我国历史上,以宗教为幌子的政治动乱并不鲜见,只是在今日,这些传统的会道门早已衰落,并且被大众所熟知,缺乏号召力。与之相反,作为西方宗教的基督教,带有西方文明的先进外衣,不为我国大众所熟悉,没有深厚的教会信仰传统和强大的教会组织,又具有足够的组织活动和理论构建空间,于是常常为邪教组织所借用。(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当代宗教研究所)